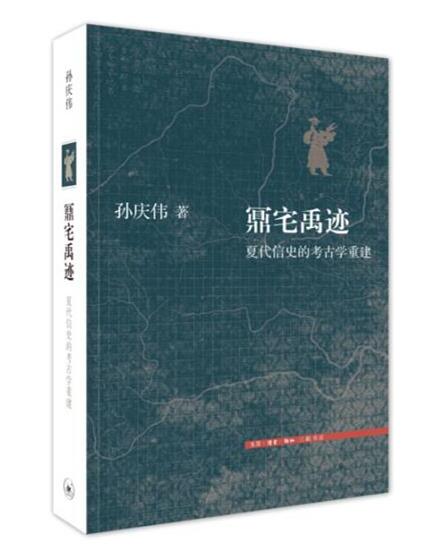孙庆伟: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怎么识别
由 分享
时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的《�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澎湃私家历史栏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先生围绕此书提问,请孙教授作答。
一、孙老师,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的,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而贝格立不但不认可郑州商城是早商文化的都邑,甚至对安阳是否能代表商城都有质疑。对于夏,该书那一章的作者张光直虽然认为二里头代表夏,但这一部分的章节却是“有史时代前夜的中国”。去年刚出版中译本的《哈佛中国史》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这可能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我们国内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有不少。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许宏就认为“中国的信史应从晚商算起,之前是原史时期”。因此,我想问您的是,您这本书副标题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相当开宗明义。您是有感于现在主流的中国古史观和蔚为大观的实证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不同看法吗?
孙庆伟:确实如此,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为了旗帜鲜明地表明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关西方学者及部分中国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欧美考古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走了一条与中国考古学家不太相同的道路,他们主张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总体上比较偏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但我想,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并不来自中国学者的个人喜好,而是由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历史资源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考古学者似乎不必因此而自惭形秽,况且,在史前考古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学者已经相当“国际化”了。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很明显看出,考古学理论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是文献史学的薄弱地区,比如史料相对缺乏的北欧,就衍生出了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和瑞典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文献最贫乏的北美则成为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而文献史料相对丰富的欧洲大陆,文化历史考古学也曾大行其道。
其次,也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认为“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将文献材料弃之不用”。他们虽然对史料也有所怀疑,但是“不能够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因为“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
第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汉学家,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文献史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所以很难在此层面上对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用邹衡先生的话来讲,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那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的缘故”。因此,在夏代是否为信史的问题上,完全不必因为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而焦虑,乃至心虚,大可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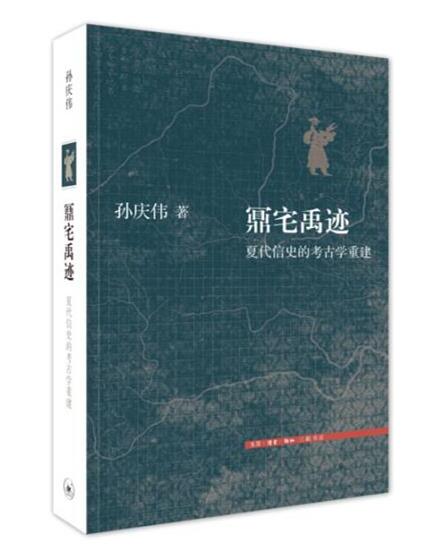
一、孙老师,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的,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而贝格立不但不认可郑州商城是早商文化的都邑,甚至对安阳是否能代表商城都有质疑。对于夏,该书那一章的作者张光直虽然认为二里头代表夏,但这一部分的章节却是“有史时代前夜的中国”。去年刚出版中译本的《哈佛中国史》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这可能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我们国内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有不少。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许宏就认为“中国的信史应从晚商算起,之前是原史时期”。因此,我想问您的是,您这本书副标题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相当开宗明义。您是有感于现在主流的中国古史观和蔚为大观的实证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不同看法吗?
孙庆伟:确实如此,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为了旗帜鲜明地表明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关西方学者及部分中国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欧美考古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走了一条与中国考古学家不太相同的道路,他们主张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总体上比较偏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但我想,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并不来自中国学者的个人喜好,而是由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历史资源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考古学者似乎不必因此而自惭形秽,况且,在史前考古和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学者已经相当“国际化”了。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很明显看出,考古学理论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是文献史学的薄弱地区,比如史料相对缺乏的北欧,就衍生出了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和瑞典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文献最贫乏的北美则成为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而文献史料相对丰富的欧洲大陆,文化历史考古学也曾大行其道。
其次,也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认为“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将文献材料弃之不用”。他们虽然对史料也有所怀疑,但是“不能够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因为“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
第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汉学家,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文献史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所以很难在此层面上对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用邹衡先生的话来讲,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那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的缘故”。因此,在夏代是否为信史的问题上,完全不必因为部分西方学者的质疑而焦虑,乃至心虚,大可不必。